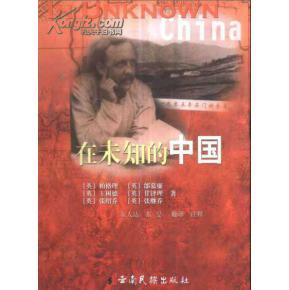|
石门坎文化现象中的苗人主体地位
贵州河湾苗学研究院院长 杨培德 摘要:一个“屙屎不生蛆”最贫穷的苗人山区石门坎,居然发展成为“西南最高苗族文化区”,然后又昙花一现地消失。这一石门坎文化现象有什么启示?本文用主体性话语对此进行分析,并强调指出,苗人主体地位和能动性的高低沉浮是这一现象起落的根本动因。 一 20世纪初的1904年,被奴役处在“地狱”中的石门坎苗人,在英国传教士伯格理的引领下,使一个“屙屎不生蛆”最贫穷的山区,成为海内外赞扬的“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而半个世纪后却黯然消失。这种昙花一现的石门坎文化现象,吸引许多学者从各种理论视角进行研究。苗族女学者沈红,运用社会学结构与主体的理论进行研究取得的成果最为突出。本文试从哲学的主体性理论,对石门坎文化现象中的苗人主体地位进行探究。作者认为,苗人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地位的高低沉浮以及苗人的主体能动性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石门坎文化现象中产生与消失的主要动因。这种主体性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今处于高风险和高竞争社会中的苗人个体自我实现和发展,仍然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主体是西方研究人的哲学话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 [1]人并不是生下来就必然成为主体,而是在社会实践的成长过程中,逐渐产生自我意识后成为自为的主体。主体的特性是能动性、整体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这些特性表现在个体身上就是自尊、自重、自立、自强、能动和创造的主体意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抬高人的主体地位,使人“成为本身的主宰,而不再消极地和驯服地等待着周围世界来使你这个人形成。” [2]主体性哲学理论使我们认识到,个体人的主体能动性力量可以自己拯救自己并能解放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是发展自己的前提,这里所指的主体还包括作为群体的主体。 二 既然主体指的是人的自主自立,那么,威宁石门坎周边地区的苗人在20世纪初是否有自主自立的主体地位,回答是否定的。我们不妨从1860年这一地区的苗人大动荡说起,动荡领头的苗人叫陶新春,“陶新春家世代都是以机土目的农奴,……陶新春的父亲是被土目折磨死的,他自己也因为不能按期缴出虎皮、狐皮等物,受过土目的毒打,陶新春兄弟三人,都曾被派到威宁州城和赫章汛地,给官吏营军服役,在途中受尽煎熬,几乎丧失了生命。” [3]不仅陶新春是农奴,黔西北地区的苗人几乎都是农奴。杨忠信对此有如下描述:“苗族来到黔西北是投靠彝族土目谋生,沦为农奴。除了向领主缴纳实物地租外,还要担负名目繁多的劳役地租。男子长期在领主家服劳役,常年不能回家。过年时只能与妻子儿女共同吃一餐饭,第二天就告别家人又去长期服役。” [4]
苗人就这样在这块土地上过着上千年牛马不如的农奴生活。历史上这些苗人并不是农奴,引领他们迁徙到贵州的祖先亚鲁王曾领导他们过着自主自立的生活,由于不断的战争失败,才沦落为农奴,上千年忍耐的积怨终于在1860年爆发,陶新春将其母亲树立为仙姑女神,运用苗族传统宗教凝聚苗人,掀起大规模争取做自己的主人的造反运动。陶新春成了苗人的“拉蒙”(苗王)和统兵元帅,在他的带领下,黔西北苗人农奴用牺牲50万人的代价,赢得了十二年自己做自己主人的尊严与荣耀。死去的苗人为活着的苗人争得了短暂的主体地位,由于官方“对贵州苗族所采之政策,舍杀戮外几无可述者也。” [5]活下来的苗人又重新跌入苦难的深渊,他们仍然沦为没有自由和尊严的农奴,仍然是牛马不如的非人。
从主体性的理论话语分析,陶新春领导的苗族起义,是黔西北苗人千年一次的大规模争取主体地位的运动。这一运动由于借助苗族本土宗教,被一些研究者称为“千年教”运动。[6]苗人借助宗教解救自己获得主体地位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宗教产生于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人在生活实践中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渺小、有限和无助,于是便创造出具有强大的、永恒无限生命力的宗教,“给人类某种助力,使人类得以有信心奋斗生存下去。” [7]在人类社会中利用宗教对压迫进行反抗是常有的事,“宗教反抗基本上是某个群体积怨的集体性爆发,目的是在于通过和平和非和平的手段,促使现存社会和社会秩序做某种改变。” [8]
黔西北苗人利用本土宗教争取主体地位反抗压迫的运动虽然失败,他们却并没有沉沦而甘心当农奴,渴求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的主体性欲念仍然念兹在兹,只不过将其深藏在心底而已。以至于事隔30年后的1902年,当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到安顺调查苗族时,他只看到阴郁沉静的苗人,听到的是“一种悲哀之感的苗人芦笙音乐。” [9]苗人坚强不屈并孜孜以求主体性解放之路的内心渴求,处于苗语世界之外的人是难以察觉的,因为苗人不会轻易将其内心的主体性欲求向陌生的外来人表露。只有在外来人承认苗人作为平等的主体,并听懂了苗人唱诵悲壮的《苗族古歌》,理解了苗人祖先在血与火的迁徙中用生命换取自主、自立的主体性英雄史诗时,他才能理解在苗语生活世界中的苗人,为什么其主体性精神还没有死的原因。 劫后余生的苗人精英,将“拉蒙”陶新春带领苗人起义的历史编成《肯拢拨朵造反歌》来传唱,这是一首苗人歌颂争取获得主体地位的希望之歌。苗人利用自己的本土宗教拯救自己受到挫折,之后仍有少数的苗族精英在四处寻找希望,他们没有绝望的原因正如德国宗教哲学家蒂里希说的那样:“因为人怀着期望前行,要超越被给定者而走向未来。” [10]而美国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也认为:“人类生存总是向着未来的……。人的这种未来性的本质方面是希望。正是通过希望,人可以战胜此时此地出现的任何困难。而且正是通过希望,人在面临极度的痛苦时发现了意义。” [11]当苗人本土宗教中的祖神给予的希望在残酷的现实中破灭时,他们只有另寻能实现自己获得主体地位希望的他者神灵,这是因为“信仰的生命在于希望。” [12]就在苗人寻找获得主体地位希望的过程中,有一个洋人正在滇黔交界地执着地寻找基督教的“迷途羔羊”,他要将基督教中的“信仰”、“希望”和“仁爱”传给这些人。这个人就是伯格理。伯格理坚持在底层人中寻找皈依者,他首先在云南昭通地区的汉人和彝人中寻找,“然而在三年的时间内他的福音传道却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可见的与实质性的成就。他投入大量的时间巡行,充满热情地不停宣讲,结果仍收效甚微。” [13]1904年,在伯格理近乎绝望的时候,有4个在绝望中坚持寻找希望的苗人,历尽艰辛找到了他。伯格理的朋友和继任者甘铎理对这4个苦苦寻找希望的苗人感叹说:“他们是自己种族的代表,这个种族后面有一段为期若干世纪被压迫与被迫害的历史。环绕着他们的世界永远是艰苦的,……苗家人除了熟悉能带来贫困与痛苦的天地外,竟不知哪里还有一方乐土。”“苗族人是在寻找他们之中无人知道的存在之物。他们的历史中没有任何线索能够启示他们相信,在世界上有一种对被压迫人众的爱,或者对痛苦的安抚。” [14]甘铎理弄不清支撑这些苗人如此坚持寻找希望的个中原因,他只能猜测说:“当为寻求自己未知的希望,日复一日地迈步穿行在深山之中的时候,他们心中必定一直充满某种奇异的激情。”甘铎理没有理解这些苗人是在抗拒命运,就像古希腊的西西弗神话那样,法国哲学家加缪说:“西西弗不断把巨石滚上山顶,而石头因为它自身的重量又会滚下去,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没有比这徒劳而无望的工作更可怕的惩罚了。然后西西弗看着石头马上朝更低的地方滚下去,在那里,他不得不把它重新滚上山顶。我看到他回到山下,迈着沉重而整齐的步子,走向他永远不知道尽头的痛苦,当他离开山顶,渐渐沉没在诸神的领地,他是高于他的命运的,他比那巨石更坚硬。” [15]如果从加缪的视角来看这些寻找希望的苗人,那么苗人们也像西西弗那样高于他们的命运,他们比巨石更坚硬。 当4个衣衫褴褛的苗人找到伯格理时,伯格理被这些苗人的执着寻找希望所感动,他看到他曾认为“在整个中国没有谁比此阶层更令人不抱希望” [16]的苗人还在抱着希望,于是他用热茶亲切地接待了这四个苗人。由于语言障碍,4个苗人只能从热茶中品尝到伯格理暖人的仁爱之心。没有仁爱之心的民国贵州官员杨万选始终不理解,为什么“蠢蠢苗族……数千年之羁縻屠杀,乃不及耶教一席话之使苗民死心塌地。” [17]其实当初与伯格理见面的苗民还不知道耶教为何物,也听不懂洋人的耶教一席话。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是,农奴身份的他们,被高贵的洋人作为有尊严“脸面”的人给予尊重和仁爱。尊重的体现就是伯格理的那一杯热茶,热茶表明双方是有尊严平等的主体,热茶表明了仁爱之心,热茶成了主体“脸面”的象征。数千年来,苗人在与苗语世界之外的人打交道时,被称为“蠢蠢苗族”的苗人,从未有过这样被作为有尊严“脸面”的人给予尊重,苗人寻找的主体希望首要的就是作为人的平等尊严的“脸面”。中国人把平等尊严称为“脸面”,传教士甘铎理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文明中最为强烈的要素之一是‘脸面’。”“部落人历来被排除在这个把‘脸面’看得如此重要的社会之外,因为正当、体面和文雅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一位汉人可以耍弄一个苗族人而不受惩罚,可以把它当作低于人类的动物对待都不会招致邻居们的任何不满。” [18]在这个人类共同生存的世界上人人都要“脸面”,苗人也不例外地要平等尊严的“脸面”,只有动物不要“脸”。清朝雍正皇帝就曾在奏折上批示说苗人与禽兽无异,禽兽何来“脸面”?到了三民主义的民国时期批示仍然有效。1912年,协助伯格理创制苗文的苗人杨雅各,在威宁街上被骂“苗狗日的”就是例证。这是由于中国数千年“孔教且素持外攘”,[19]信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必然结果。
在充斥“禽兽论”的社会,伯格理没有把前来寻找希望的苗人视为禽兽,而是把苗人视为“上帝心中的花朵”。而苗人也把伯格理作为“奇特的外国朋友”,苗人对伯格理说:“我们起初感到害怕,不久后来我们来到这里,看见并发现您不是一个外国人,而就像我们自己人一样……同样的一家人,只不过你来自远方。” [20]就这样,在必然的偶然中,在互为平等的主体间性基础上,伯格理主动地选择了苗人,苗人也主动地选择了伯格理。
三
“黑暗时代谁可怜我们,困难环境谁同情我们。”这是石门坎苗族信教史碑记载苗人迫切希望作为人的主体性生存的呐喊,伯格理是这一呐喊的唯一回应人,他将这一呐喊引导形成了一场基督教传教运动。甘铎理认为:“这场运动的产生,看来它似乎是在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压迫和绝望后,为了挣脱他们身上的枷锁和要求过上更为高尚的生活的突然爆发。这里有为了被压迫者的新生活,有为了被遗弃的人的希望。”甘铎理还认为,如果不是伯格理把苗人的希望引向基督教,“这场运动可能最终要成为一次失败的农民起义。它将是一场反对他们历史宿敌的暴动。有时候这些荒野中的人过着与动物相近的生活,又被一个强大的政权当作少数异类来抑制,终于变得忍无可忍;他们猛然奋力向监禁自己的围城撞去,却又被反弹回久受漠视的禁区。” [21]伯格理何以能避免苗人再一次爆发“撞向围城”的起义,而将苗人寻求改变被压迫主体的农奴地位的愤怒,引进基督教的窄门并形成运动。其中有多方面的因素,而重要的是伯格理的底层人人格魅力和仁爱之心吸引了苗人,伯格理具有社会底层人的身份人格,心理学认为“身份人格对社会的正常运转极其重要。” [22]伯格理出生于英国底层的工人家庭,他家的生活标准相当节约简朴,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23]伯格理中学毕业因贫困未进大学,他宁愿放弃薪水丰厚的文官工作,而自愿去为贫穷的底层人传教。他选择了为被剥夺话语权的“天生能说话的”被压迫主体说话。[24]他的这种底层的身份人格,使它具有“完美天性,即和蔼、友好与灵敏,尤其是他十足的幽默,成为他与周围那些人打成一片的秘密。” [25]当伯格理遇到被压迫在底层无法生存的苗人时,他对压迫者的义愤与对被压迫者的爱就在他人格的情感中激发出来,“义愤这种情感植根于对人类的爱”。[26]他把这种爱倾注在苗人身上,尽管苗人衣衫褴褛,他却亲切地称苗人为“上帝心中的花朵”。[27]由于爱,他喜欢苗人,也由于爱,苗人喜欢他,这种相互喜欢在心理学上叫做人际吸引的相互原则。 伯格理爱上了苗人,他穿苗衣、吹芦笙、吃荞饭、住牛棚、办学校、办医院和孤儿院、办生产改良所等等。甘铎理评价说:“伯格理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他们得以进入这个相互尊重和有‘脸面’的世界。当苗族人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他们往往变得比乡村中较为贫穷的汉族人更有教养。一个人既然有资格成为外国人的朋友,也就有资格受到单独的礼遇,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以来,经过若干个世纪的摩擦与冲突,汉人第一次被迫把受欺压的邻居当作与自己一样有体面的人来对待。” [28]在伯格理打开的大门里,苗人体验到了人人平等的友爱,就如拉克坦乌斯说的那样:“在上帝眼里,谁也不是奴隶,谁也不是主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 [29]苗人在这个主体间性的平等生活世界里,可以亲身感受到一个汉族布道员以庄重文雅的方式给过路的苗人鞠躬问好,教徒中的汉族、彝族和苗族人彼此都彬彬有礼,汉人地主的少爷小姐、彝人领主的少爷小姐与苗人农奴子女平等地同桌读书。在这个世界里人与人充满了友爱。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说:“爱的需要涉及给予爱和接受爱……,我们必须懂得爱,我们必须能教会爱、创造爱、预测爱。否则,整个世界就会陷于敌意和猜测之中。” [30] 其实不只是伯格理打开的大门里有仁爱,在苗语生活世界的传统里也一样充溢着仁爱。苗人的人际关系就是一种诚挚的平等互助互爱关系,苗人用这种友爱来团结群体应对艰辛的生活。伯格理的同事哈兹佩斯在《石门坎与花苗》中对这种友爱的关系作有如下记录:“在彼此打招呼时,苗族人总是怀着满腔热情。”“苗族人惊人的好客。”“苗家人总情愿倾其所有,以使来访者得到款待。” [31]
在黑暗的年代,苗人真诚地用这种友爱去爱苗语世界之外的官家、地主和农奴主,然而回报的却是血淋淋的恨。血的代价让苗人明白,只有自己被他人当作有尊严脸面的主体,在交往中彼此承认对方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时,真正的仁爱才可能存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说:“我们能否共同生存而又各自保持我们不同的特点,全看我们能否互相承认彼此都是主体。” [32]用苗人数千年的历史可以证实这句话是历史经验的经典总结。
苗人与伯格理在石门坎,共同建构了一个主体间性的平等友爱的和谐社会,为此成百上千的苗人涌入石门坎。伯格理喜形于色地说:“一个奇迹正在中国西部被铸就出来” [33]伯格理并不满足于此,他还利用他的洋人传教士身份,为苗人争取平等的国家公民主体权利。他对中华民国政府无视西南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不满,致电质问外交部长伍廷芳:“西南各族同居中华领土之上,亦应有一色标记列为国旗之上,今仅以五色代表五族,而苗彝反非国民乎?” [34]石门坎苗人跟随着这样的质问,提出了国家应承认其主体地位的要求,朱焕章就在《滇黔苗民夜课读本》中提出:“不问男女老少,不分士农工商,人格是平等的,不问天资的智愚,不分境遇的好坏,都有发展的机会,这是社会的平等。不问宗教、种族,不分贫富贵贱,都受法律同样保护,这是法律的平等。”
伯格理为苗人争取平等的主体地位“赢得了苗人的心,而此前此后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35]最能赢得苗人心的是伯格理和苗人一起共同创造了苗文。古宝娟和饶恩召在《苗族救星》中说:“然至今尚无苗民文字,既无文字,何来文化?所以柏牧师不但熟悉苗语,更进一步创造文字,他认为这是他毕生最紧要的工作。” [36] 苗人之所以是苗人,是因为苗人用苗语认识和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苗语生活世界,苗人的心灵及其文化全部展现在苗语生活世界中。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世界是不完整的世界,讲主体间性的平等首先必须讲语言文字的平等。苗语被历史上的统治者污名为“人皆 舌”的鸟语,并且认为有“肃杀之气”的苗语令苗人造反,[37]因而不断地企图禁止苗语和苗文。伯格理和苗人排除阻力创造了苗文,这种苗文简便易学,苗人很快掌握了这种文字,哈兹佩斯评价说:“根据他们的语言产生的文字结构而变得自豪起来。” [38]苗人为能用自己的文字学习知识而自豪自信,然而民国贵州省政府却要将苗文铲除,石门坎培养的苗族知识分子张斐然据理力争说:“我认为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字是拼音文字,石门坎苗文是拼音文字,所以属于进步文字的行列……命令加上刺刀也是消灭不了的” [39]由于理屈,民国贵州省政府只好作罢。
四 石门坎苗人在伯格理打开的大门里,有了平等的尊严和主体地位,苗人被长期压抑的主体意识得到张扬,自豪取代了自卑,“果敢自立取代了相当畏缩的任人支配”,[40]苗人蕴藏的潜能和主体能动性终于喷发出来,他们如饥似渴地用自己的文字掀起了学习热潮。他们学习的动力就来自要争取自己主宰自己的主体性夙愿。比如在金陵大学读书的石门坎苗族青年李正文,他读书的动力就来自其父亲的一句话:“苦日子由老一辈过就算了。你们这一代不能再当奴隶,不能世世代代再受官家、土目、地主欺压当牛做马,不能再当睁眼瞎没文化的人任人宰割了。……你一定要下决心去读书,有了文化知识,才会受到人的尊敬。” [41] “不再任人宰割”,“受到人的尊敬”。这些话说出了苗人千百年来的主体性诉求。发愤读书的苗人成了苗人中的佼佼者。1929年,苗族数千年历史以来产生了第一个博士吴性纯。他从目不识丁的山野牧童,成为西医的医学博士。在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八年的苦读,其间的刻苦可想而知。获得博士不留在城里,毅然回到“屙屎不生蛆”的石门坎,为苗人医病并兼任小学校长。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支撑他这样做?个体主体的吴性纯充分发挥潜能获得了成功,然而众多苗人群体主体仍然处在贫困中,吴性纯如果没有对群体苗人的爱心,只为自己不为他人,他完全可以逃离贫困一走了之。苗人的佼佼者不只是吴性纯,教育家朱焕章、学者杨汉先和革命家张斐然等人都返回故里,报效乡梓。
石门坎文化现象的主流,就是一大批苗人农奴被压抑的主体性得以张扬,吴性纯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就是其中的代表。在黑暗的年代,苗人的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不能通过《圣经》根本改变国家社会制度结构而获得自己的全面解放。哈兹佩斯在《石门坎与花苗》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苗族人终究看出《圣经》不是医治他们所有苦难的万灵药。并非每一朵花都是玫瑰,也不见得每只鹅都是天鹅。虽然他们信奉上帝,但苗家毕竟还处于一种奴隶身份。” [42]伯格理对于致使苗人贫困的旧中国国家社会制度结构也感到无奈,他在日记中哀叹道:“这种贫困程度是令人难以想象到的。那些房屋中有不少座连一元钱也不值,但土目正是靠着多年来对这些人的压迫,过着富裕的生活。……我感到无比的气愤和棘手。难道从来就是这样吗?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些人的希望了吗?如果我们宣讲在天国里没有财主的位置,群众就可能嘲笑我们像是在另一个世界讲话,而他们在人世上到底有什么机遇呢?” [43]苗人的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在剥削与压迫的国家社会制度结构控制下,根本摆脱不了贫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说,“国家是人类谋生的单位,” [44]苗人在这样的国家里却无法谋生。那些信奉基督教的苗人的希望只能在飘渺的天国。
所以,当伯格理去逝后,“宗教信仰的大海落潮了。” [45]尽管宗教信仰落潮,但由伯格理点燃的苗人自尊、自主、自立的主体性之火,仍然继续燃烧。特别是石门坎苗人读书的热情不减,据张坦统计,从本世纪初到1949年,乌蒙山区三分之二的苗族皆能草读《平民夜读课本》。达到扫盲标准,高初小学毕业生数千人,受中学教育的200余人,高等教育的30余人,博士2人。苗族人口中受教育的远远超过其他少数民族,甚至远远超过汉族。[46]这一现象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只要苗人充分发挥主体自我的主体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继而影响苗族群体的命运。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奥托说:“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的一系列最新成果证明人类的潜在能力是巨大的。”“一般健康人只在运用着他的潜能的极小一部分。……一个人所发挥出来的能力,只占他全部能力的百分之四。” [47]虽然个体的人生活在以国家为谋生单位的社会之中,受到国家不同时期既定的社会制度结构所制约,但个体的人,仍然可以在制度结构给予的发展空间里,尽最大的努力去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俄国心理学家科恩就认为:“主体地位本身并非作为自然的授予而为任何人所固有。主体地位总是要争取的,而要保持这种地位也需要作一定的努力。” [48]这样看来,个体及其群体的人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主体能动性,努力争取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才有可能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发展,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石门坎文化现象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深刻的道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葛兰西《狱中札记》转引自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 (3)《陶新春起义与黔西北苗族》 (4)《咸同烽火》毕节地区苗学会编 (5)(17) 杨万选《贵州.苗族考》 (6)张兆和《杨汉先关于黔西苗族身份认同的书写》 (7)李亦园《宗教与神话》 (8)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9)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 (10)蒂里希《蒂里希选集》 (11)参阅莫尔特曼《希望神学》,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 (12)贝格尔《天使的传言》 (13)(16)(23)(27)(33)(43) 伯格理《在未知的中国》 (14)(18)(20)(21)(25)(28)(35)甘铎理《在云的那一边》、《在未知的中国》 (15)加缪《西西弗的神话》 (19)摘自石门坎溯源碑 (22)林顿《人格的文化背景》 (24)斯皮瓦克《斯皮瓦克读本》 (26)马雷特《心理学与民俗学》 (29)迪蒙《论个体主义》 (30)戈布尔《第三次浪潮:马斯洛心理学》 (31)(38)(40)(42)(45)哈兹佩斯《石门坎与花苗》 (32)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 (34)(46) 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 (36)古宝娟、饶恩召《苗族救星》 (37)徐家干《苗疆闻见录》 (39)转引自《威宁文史资料》 (41)《天生桥学校105周年纪念》 (44)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 (47)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 (48)科恩《自我论》 |